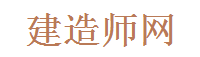《宣庙中兴志》是成书于朝鲜王朝中后期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宣庙”即朝鲜宣祖大王(1567—1608年在位),“中兴”指16世纪末朝鲜壬辰抗倭战争的胜利。该书记事范围上起宣祖二十年(万历十五年,1587),下至宣祖四十年(万历三十五年,1607),详细记録了朝鲜、明朝、日本三方在壬辰战争中的交战、议和活动,同时也交代了战前日本与朝鲜交涉请款,战后双方遣返俘虏与恢復国交的来龙去脉,且书中对重要事件多有考证,对於研究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等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由此,国内外学界多借之以考察相关史事,但迄今为止,管见所及,仅有蒋逸雪(1902—1985)、李光涛(1897—1984)曾专文探讨过朝鲜钞本《宣庙中兴志》,然二文所论均存不尽準确处,有必要对该书作进一步考察。本文谨以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二卷本为主,就该书之撰写年代与作者、史源与史学价值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等问题展开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宣庙中兴志》撰成后以钞本形式传播,现存诸钞本有二卷、三卷、六卷和不分卷几种。今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庆尚大学图书馆存二卷本各一部,首尔大学奎章阁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存六卷本各一部,成均馆大学尊经阁存三卷本一部,此外,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另存四册本一部,首尔大学奎章阁、啟明大学图书馆、庆尚大学图书馆各藏零本一册。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修订本亦收録朝鲜传钞本《宣庙中兴志》,属两卷本系统,但未注明影印底本来源。受条件所限,笔者目前经眼者有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二卷本、四册本(属不分卷系统)和《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影印本三种,其中,四册本乃一简略节本,无书序,注文亦存缺略,《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影印本漫漶不清,无书序。唯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二卷本序文、正文俱全,字迹清晰可辨,故本文谨以其为主进行讨论。
二卷本《宣庙中兴志》分上下两册,上册记丁亥1587年至壬辰1592年,下册大部记癸巳1593年至丁未1607年,最末乃佚名《南汉録》、《江都録》,专记丙子胡乱事,因其与本文无直接关联,故不赘。该书在体例上按时间排列,在具体条目上“提纲立目”,即先列纲以明大体,次立目详细説明。正文之外,又有双排小注和天头注文,对正文内容加以考订説明。总之,《宣庙中兴志》详细记述了壬辰倭乱的事件本末,以平实的语言刻画了李舜臣、郑拔、金千鎰、边应井等朝鲜官兵和赵宪、郭再祐等义兵将领奋勇作战的英雄形象;还原了朝鲜派李德馨、郑昆寿等奏请使向明朝请兵,明朝君臣对此事件的争论,李如松、杨镐、骆尚志、麻贵、刘綎在朝期间的抗倭战斗与事迹,以及沉惟敬与日军的交涉议和活动,对於我们研究明末抗倭援朝战争颇有助益。
关於《宣庙中兴志》的成书时间,李光涛未有提及,蒋逸雪认为“盖书成於晚明,不久满人主政,中论当日边事,有触忤清廷者,自不能出”。此説有误。首先确定其撰写下限。正祖末年时值壬辰战争两百周年之际,原任直阁尹行恁奉王命编纂《李忠武公全书》,并于正祖十九年(1795)由柳得恭监印刊行。书中辑録《宣庙中兴志》中有关李舜臣的内容作为附録的一部分,经笔者核对,其引用文字“全罗左水使李舜臣啟曰:‘遮遏海寇,莫如水战,水军决不可废也。’上从之”等21条皆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二卷本相合,可推知《宣庙中兴志》的成书下限是1795年。该书之撰写上限,则需据其引用书目加以判定。《宣庙中兴志》中曾徵引柳成龙《惩毖録》、赵庆男《乱中杂録》、李端夏编《宣庙宝鉴》、李玄锡《明史纲目》及李喜谦《青野漫辑》等书,据韩国歷代人物中央情报系统,《青野漫辑》成於1739年,在诸书中成书最晚,则《宣庙中兴志》完成时间不早於1739年。故《宣庙中兴志》大致在1739—1795年间撰成,相当於清代乾隆时期,而非晚明或壬辰战争后不久即告成。
至於该书作者,根据韩国古籍综合目録系统的着録,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四册本、啟明大学童山图书馆藏本题为未详,成均馆大学尊经阁藏本、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近代俞镇泰钞本及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二卷本均题为丹室居士,唯庆尚大学图书馆藏本题为辛锡谦(1754—1836)撰。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所收《宣庙中兴志》书前提要指出该书作者乃权文海(1534—1591),又云该钞本“不载撰人姓名”,然权氏乃朝鲜中宗、宣祖时人,壬辰战前即已亡殁,其着録之错谬可想而知。此外,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二卷本《宣庙中兴志》书前序曰:“余於戊午时有殤戚意,忽忽不乐,思有以着书忘忧,乃取宣庙朝靖乱事迹之散出公私文字者,无幽细尽閲之……乃復考据日月,刊其繁杂,削其浮夸,而撮其精要可传者,提纲立目,稡为成书,名之曰《宣庙中兴志》。非特以一时着述为间漫寓之资而已,将以播告於后之秉笔史者,俾有所采择云尔。丹室居士书。”序文明确指出了丹室居士开始撰写《宣庙中兴志》的时间和缘由,故可断定该书作者即“丹室居士”。又,序中所言“戊午”在18世纪对应1738、1798二年份,由前述撰成时间可排除1798年,而1738年又与辛锡谦生活年代不合,故知辛氏絶非丹室居士,其或是《宣庙中兴志》辗转迻録过程中的誊抄者之一。那么,丹室居士究竟何许人也?
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一所收《会友録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綫索。该文交代了撰序者与洪大容合作编撰“东国诗”的始末。据韩国学者权纯姬等考证,二人所编诗集乃《海东诗选》(又名《大东诗选》),今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最值得注意的是,序文落款“丹室居士閔百顺顺之甫”告诉我们,閔百顺即丹室居士。閔百顺(1711—1774),字顺之,号丹室居士,又称成川,本贯驪兴閔氏。两班贵族出身,曾祖父驪兴府院君閔维重(1630—1687)乃肃宗李焞之妻仁显王后生父,祖父閔镇远(1664—1736)在英祖朝官至右议政,外祖父金昌集(1648—1722)乃景宗时领议政,生父閔昌洙(1685—?)官至前行世子翊卫司副率(从六品),皆为老论派的重要人物。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閔氏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英祖十七年(1741)辛酉科进士及第,后歷任明陵(肃宗王陵)参奉、刑曹佐郎、工曹正郎、金山郡守、延安府使、杨州牧使、同副承旨(正三品)等职,英祖五十年(1774)去世。与洪櫟(洪大容之父)、洪大容(1731—1783)、安锡儆(1718—1774)、蔡济恭(1720—1799)等相交游。閔氏博闻强识,学问深厚,正祖亦夸讚其“言若不出口,而叩其中则甚博恰”。閔氏生平着述除《海东诗选》外,还撰有《丹室集》,惜今未见流传。
閔百顺生活的时代,是朝鲜王朝小中华意识急剧膨胀的时期。明清鼎革后,基於传统华夷观及对明朝“再造藩邦”的感恩,朝鲜王朝呈现出强烈的尊周思明心态,特别是18世纪英正时期,朝鲜朝野借助各种渠道表达对明朝的追怀与感念,包括建造大报坛与万东庙、编修中国史书等。这种思明情绪在閔百顺家族中有鲜明的体现,特别是其外祖父金昌集之先人金尚宪(1570—1652)乃丙子胡乱(1636—1637)时对清斥和论的代表人物,先后两次作为人质被清军押解至瀋阳,曾祖父閔维重、祖父閔镇远均为积极宣导“北伐论”的大儒宋时烈(1607—1689)之门人。处於这一时代氛围下,加之家族记忆的影响,閔百顺十分强调华夷观和尊明贬清思想。华阳洞万东庙乃宋时烈门人权尚夏所建,作为朝鲜儒林祭祀明朝皇帝的场所,甚至庙内种植的桃、竹、稻、花等植物均被冠以“大明”字样,从而赋予丰富的象徵意义。閔百顺亦曾作诗咏叹大明稻,其曰:“四海穷阴此一阳,葩溪有庙享明皇。西山采蕨清风在,南国留禾旧泽长。名袭大邦依日月,播同千亩备籩框。年年香火星坛下,添得王春侑宓芳。”诗句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朝鲜对明朝的感恩及朝鲜保留了大明餘脉之意。由此,尊周思明成为閔氏撰写《宣庙中兴志》的重要文化背景,书中凡遇“天朝”“皇朝”“皇上”“帝”皆空格或另行书写,即所谓“书法矜慎,华夷较然,深得《春秋》之义”。
而另一方面,朝鲜王朝自宣祖以来就党争不断,形成“南北老少”四色党论,到景宗年间(1720—1724)和英祖即位前后,少论与老论围绕王储问题爆发了激烈党争。作为老论派的重要势力,閔百顺家族与党争息息相关。景宗元年(1721),由於景宗身体孱弱且无后嗣,以金昌集为首的老论派主张以景宗庶弟延礽君(即后来的英祖)为王世弟并代理听政,此举遭到少论派强烈反对,最终酿成“辛壬士祸”,金昌集、李颐命等大臣被少论诬衊意图谋害延礽君,而以谋逆罪赐死,閔氏祖父閔镇远亦流配星州(庆尚北道),直到英祖即位后才得以平反和恢復官职。金昌集在临终前曾致信外孙閔百顺:“前后书,近缘心扰,未克作答,汝必为鬱也。每见汝书,伤时之意,溢於辞表。今余将死矣,汝作何如怀耶?须勿永伤,惟以保护汝慈为意,俾得保全,则余目可瞑矣。汝能嗜文字,此则必不待余劝而成就无量也,只冀慎护。汝字以顺之为定,可也。《登楼赋》未及考送,可叹。”金氏以哀伤的口吻向外孙嘱咐了身后事,同时流露出对年少的閔氏有志向学的无限欣慰,并亲自为其取“顺之”为字,足见祖孙之拳拳亲情。英祖十二年(1736),祖父閔镇远去世,英祖十八年(1742),閔氏之父閔昌洙因固守老论党习,违背英祖“荡平策”,被流放至济州岛大静县,閔百顺亦屡遭牵连,多次外放。青少年时期的閔百顺可谓身世浮萍、屡遭变故。按閔氏的生活年代,知其在《宣庙中兴志》序中所言“戊午”乃英祖十四年(1738),大致符合“有殤戚意,忽忽不乐”之事境,至“戊午”本事具体所指,尚待进一步考证。
在时代风气与家族遭际的共同作用下,与其祖父閔镇远一样“取古人穷愁忧患着书述史之意”,閔百顺从英祖十四年(1738)开始专注於壬辰战争史事的书写。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时期的尊周思明愈来愈旨在突出朝鲜自身作为明朝文化继承者的优越地位,因此,《宣庙中兴志》不再致力於歌颂明军实际的援朝事迹,其书写的重点转向朝鲜本土的忠臣义士。閔百顺在书序中写道:“窃以为天朝再造之恩、圣主事大之诚,固已昭揭简,且朝鲜有餘藴。”而“至如国家之防御得失,良将策士,草野奇㑺,忠义奋发之人,及贞臣节妇树立之卓尔者,往往记有详略,迹有显晦,则容或有未尽揄扬者,终恐旷世之后,寝远寝微,而遂失其传也”,以故搜罗上起《惩毖録》、《乱中杂録》,下至《明史纲目》、《青野漫辑》等百餘年间的多种史料,广征博引、多番校正,最终撰成《宣庙中兴志》。而关於其确切成书时间,史无明文记载,只能大致界定在1739年至閔氏卒年1774年之间。
朝鲜作为壬辰战争的主战场和当事国,不仅《朝鲜王朝实録》、《承政院日记》等官方文书中详细记载了战争始末,当时亲歷战火的朝廷官员、义兵将领甚至普通平民等,也对自身的战争经歷与见闻多有记録,所以朝鲜国内关於壬辰战争的官私史料可谓汗牛充栋,卷帙浩繁。在这种情况下,对於旨在整理“宣庙中兴”事迹的閔百顺而言,搜集、爬梳、考证各类相关史料也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在笔者所寓目之三种《宣庙中兴志》中,唯《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影印本卷末附“引用诸书”一款,説明其史料来源,但该书单似未将全书所引文献悉数列出。现综合整理该书之参考书目列表如次:

以上共计引用书目50种。此外,閔百顺还徵引了大量家状、墓表、传记等资料,如李忠武(李舜臣)家乘、李五峰(李好閔)家状、洪义将(洪季男)家传、元氏(元豪)家状、金松庵(金沔)家状,等等。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閔氏上引诸书除茅元仪《武备志》外,其餘皆为朝鲜文献。这主要是因为,閔氏着力表彰发明者乃朝鲜本国之“防御得失,良将策士,草野奇㑺,忠义奋发之人,及贞臣节妇树立之卓尔者”,故而参考对象势必以本国文献为主;另一方面,这可能也跟与之相关的《明神宗实録》、《明史》等中国史书不易获得有关,朝鲜直至纯祖二十九年(1829)才从清朝买回《明实録》全帙,在此之前,他们不可能接触到《明神宗实録》,而清修《明史》在英祖十四年(清乾隆三年,1738)尚未告竣,朝鲜官方虽在英祖十六年(1740)贸得全套《明史》,并于翌年奉藏于弘文馆瀛阁,但当时《明史》在朝鲜仍未广泛传播,这也从侧面暗示了《宣庙中兴志》的撰成时间很可能正是在1740年代。
其次,书中所引朝鲜文献种类多样,大体以私家史书、私人文集和家乘、家状为主,官修史书仅《宣庙宝鉴》一部,而未见参考《宣祖实録》、《宣祖修正实録》等资料。其原因在於,《实録》修成后深藏史库,连国王都难以查看,閔氏自然无法得见。《宝鉴》主要依据《实録》编纂而成,辑録歷代国王的嘉言善行以为龟鉴,经常出现在经筵日讲等君臣讨论中,故在士大夫中也多有流传。在官修史书外,閔氏所引私家史书、文集等,以亲歷过壬辰战争者居多,故而史料的原始性很强,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宣庙中兴志》在史实上的可靠度。
第三,《紫海笔谈》一条仅见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二卷本下册第79页,此页内容其餘两本均无,或是传钞过程中的脱漏。
在广泛搜罗以上文献的基础上,閔百顺在《宣庙中兴志》中参稽各本记载之异同,针对史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做了大量考证工作。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尝言:“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於后来之笔。”与《惩毖録》、《乱中杂録》这类由亲歷者撰写的“当时之简”相比,作为“后来之笔”的《宣庙中兴志》,在史料的原始性上固然无法与前者相比,但由於成书较晚,比较鉴别诸家文献、考订精审则成为它的主要特色。就此而言,该书可谓朝鲜王朝关於壬辰战争的重要考异着作。借助书中的考订条目,我们也可瞭解閔氏对官私各类史书的态度。
厘清交战双方的行军路綫与作战时间,乃战争史研究的基础问题。因此,閔百顺在《宣庙中兴志》中也对此多有关注。下举两例:第一,书中壬辰年(1592)十一月条言:“郑起龙大破毛利辉元于尚州,復其城,辉元退保开寧县。”注文辅助説明了如此行文的原因:“睡隐《看羊録》云辉元在尚州。又考《乱中杂録》云,壬辰十二月辉元屯开寧,出榜诱民,以此观之,则盖挫于此战而退保开寧矣。”閔氏结合姜沆《看羊録》、赵庆男《乱中杂録》关於日军将领毛利辉元(1553—1625)的两处记载,认为毛利辉元在尚州大败后,士气受挫而退居开寧,由此建立起不同史料间的逻辑关联,从宏观上勾勒出其在战争中的活动轨迹。翻检《惩毖録》、《再造藩邦志》对尚州之战及毛利辉元部日军之动向均未着墨,益可见《宣庙中兴志》的重要性。第二,关於宋应昌、李如松所部援朝明军究竟何时从朝鲜撤回,诸史説法不一。对此,《宣庙中兴志》写道:“(癸巳,1593)九月,宋应昌、李如松撤兵还去。《藩邦志》、《明史目纲》(笔者按:应作《明史纲目》)皆作十月,《杂録》作八月,而独《宝鉴》作九月,当从之。”閔氏通过考辨诸书,最终采信《宝鉴》之记载,体现出其对官修史书的信任。今检宋应昌《经略復国要编》是年八月二十日《报三相公书》云:“仰籍庙謨,事已就绪,餘兵尽撤。某待发善后小疏,亦即西旋。伏祈相公请一明旨,命某回还覆命。”宋氏表达了在日军“尽撤”的情况下意欲西行归国的请求,但直至此时朝廷仍未明令大军撤退,《乱中杂録》所谓“八月二十二日,宋应昌、李如松领兵马还辽东”,如非误记,则应指明军在朝鲜由南向北收缩战綫,并非业已还辽,否则宋氏必於八月二十日发信当日或次日即收到朝廷詔令继而迅速渡江回国,无论从朝廷的处理效率和信件的送达速度来看,这都是难以实现的。考《宣祖实録》二十六年(1593)九月二日云:“礼曹判书郑昌衍(八月二十六日,在定州)驰啟曰:“提督与巡按,本月二十四日,发平壤抵宿肃川,二十五日向安州,今日到定州,经略则昨已西还矣。”其中提督、经略分指李如松和宋应昌,是知在李氏八月二十六日到达定州时,宋应昌已先一日离开定州啟程西行。又,宋氏九月十二日《报辽东周按院书》言:“某十三日渡江,晤期想亦不远”,知明军最高指挥宋应昌於九月十三日渡江还辽,是为明军撤离朝鲜的标誌,随后除刘綎、吴惟忠部外其餘各部明军陆续归国,即使如申钦所言李如松於“癸巳十月,班师”,亦属撤离的后续事宜。因此,閔氏所主张的明军九月还去之説大致无误。
《宣庙中兴志》中对壬辰战争初起时全罗道海南县监边应井(1557—1592)殉难事迹的考订,最能体现作者的考证功力及其对各类史料的态度,谨録之如次:
边公事迹一出於《宣庙宝鉴》,一出於《惩毖録》,而二説各异,《宝鉴》所记即此是也。《惩毖録》曰,贼兵入全州界,金堤郡守郑湛、海南县监边应井御于熊岭,栅断山路,终日大战,射杀无算,贼欲退。会日暮,矢尽,贼更进攻之,二人皆死云。公之家状一遵此説,而尤翁亦依其家状为墓文,则庶为明证。然尝见《乱中杂録》叙熊津事迹,日月比诸説最为详备可信,而公名不与焉,是诚可疑。(后详列“四可疑”,略)……盖《乱中杂録》即南原士人赵庆男所着,而泽堂所称信史也。南原近於全州,故其所记载皆伊日所闻见,而尤为亲切可信。《惩毖録》所録不过一时风传,而语亦草略,公之家状只祖《惩毖録》而已,且多有模糊无凭者,则恐未可谓明证也。以《杂録》之信笔而终不载之,《惩毖》、家状之不可全信又如是,则公之不死於全州必矣。既不死全州,则《宝鉴》所谓死於锦山之説是也。盖重峰既以八月十八日殉节锦山,而公又继进以死,则墓表所谓七月二十七日果在重峰殉节之后,而继死之迹甚明,此可一验也。且锦山人立祠以公与重峰、霽峰而侑之,两贤皆是锦山殉节之人,而公亦一体受享,则其不死於全州而死於锦山可谓明矣。此二验也。且《宝鉴》文字皆是实録中抄出者也,实録乃泽堂纂修而广搜稗乘野説,笔削以成者,既叙熊岭事实而不载公名,必於此而特笔书之,则是必有明据而然矣。此三可验也。
閔氏综合考辨《宣庙宝鉴》、《惩毖録》、《乱中杂録》,边应井家状、墓表等多种官私史料,且注意到锦山人的立祠风俗,依次列出“四可疑”质疑《惩毖録》之可靠性,又以“三可验”的确凿证据考订出边应井并非死於全州,而是在锦山之役中壮烈殉国。为验证閔氏的结论,我们可将其论证与《实録》内容相互参照。据《宣祖实録》二十九年(1596)四月六日司宪府啟文:“咸兴判官申忠一,前任康津,当壬辰变初,与海南县监边应井,于锦山赴战之日,作为一军,约同死生。应井恃忠一协力相援之言,先登接战,贼势不甚众盛,忠一若即进救,贼未必肆凶,应井亦不至於败死,而应井之大呼请援,佯若不闻,指兵退遁,使一军尽溃,南方士卒,至今愤駡。”又,《宣祖修正实録》二十五年(1592)八月一日载:“海南县监边应井追至击倭,死之。应井初与赵宪约共攻锦山,既而与官军皆后期,闻宪败死,叹曰:‘奈何与义将约而背之,不俱死乎?’即提兵独进至城下,格斗而死。”由於赵宪死於八月十八日,《修正实録》将边氏殉节日期系之八月一日显属讹误,但其对事件原委之描述当可信从。综上,我们可梳理出边应井临终前的主要事迹,即边氏与义兵将领赵宪相约攻打锦山,未至而赵宪已先捐躯,其后边氏又与申忠一约定共攻锦山,但申忠一在攻城作战中观望不前,致使边应井孤军身死。由此可知,閔百顺上文针对边应井殉节事迹的考证合理準确。事实上,类似考订在《宣庙中兴志》中仍有不少,它们对今人重建关於壬辰战争的叙述颇富价值,理应获得重视。
另外,从前述引文也可看出,閔百顺最终采信了《宣庙宝鉴》和《乱中杂録》的记载,表现出对实録、《宝鉴》等官修史书和亲歷其事者的信任;与之相对的是,否定了柳成龙所撰《惩毖録》的可靠性,认为其“不过一时风传,而语亦草略”。显然此处对《惩毖録》评价较低,但亦不可一概而论。柳成龙作为亲歷战争的朝政要员,当时可以接触到大量官方文牘奏疏,这是其他撰作者所不具备的条件,所以《惩毖録》自有其价值在,不能一味指为“风传”之作。事实上,该书问世后被认为是有关壬辰倭乱的最基本文献,后来甚至流传至日本,且现今学者也多肯定其史料价值。然而,閔氏不惟对《惩毖録》评价较低,书中为数不多的提及柳成龙处亦多持负面意见。如,“宋应昌遣沉惟敬入贼营议和……适平秀家等投书於倡仪军中乞和,柳成龙得其书,献於督府,如松遂与宋应昌决意讲和。”言下之意,柳氏间接促成了议和局面的形成,其应对此负责。又如“(丙申1596)八月,杀忠勇义兵将金德龄……李时言、金应瑞尤忌德龄,欲乘时杀之,密啟言德龄有反状,领议政柳成龙力主其言……大臣郑琢、金应男等力言德龄必不叛,柳成龙独不对。”即柳成龙出於党派成见而力主杀害义兵将领金德龄,在大敌压境下残害忠良。但这两点均非柳氏个人独有的看法或由其一人造成,而是当时条件下整体环境与决策的结果,事实上,柳成龙作为时任朝鲜领议政,为抵御日军侵略,采取了包括起用李舜臣、权慄等将领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为抗倭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故閔百顺在书中对柳成龙及其《惩毖録》的苛责恐非持平之论,究其原因或与党派立场有关。要之,柳成龙是宣祖时东人党领袖,而閔氏所属之老论派乃西人党的分支,而西人党又为东人党之死敌,不同的党派立场或影响了閔氏的歷史书写,从而导致书中对东人党多批评之辞而对尹斗寿、赵宪等西人党多正面论述。这是需要加以留意的。
《宣庙中兴志》成书后,以其独特的史学价值流传於世。如前所述,编纂于正祖时期的《李忠武公全书》即曾引用之。该书主要以钞本形式传播,不仅在朝鲜半岛流传,更远播中国,成为近代中朝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
让我们回到前述蒋逸雪、李光涛所见朝鲜钞本《宣庙中兴志》,从版本形态来説,该本分上下两卷,属二卷本系统,蒋、李二人的誊録本属其分支。20世纪40年代初,蒋逸雪曾供职于张继(1882—1947)主持下的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故得以见到大量稀本秘笈。关於钞本《宣庙中兴志》,蒋氏曾详细説明了其来源:“沧州张溥泉先生继,往游扶桑,道经斯土,缅箕子之流风,慨政教之匪旧,爰访遗逸,托搜秘藏。有俞镇泰者,三韩名士也,以《皇明陪臣传》及本书相貽。”是蒋氏得自张继,而张继又得自朝鲜俞镇泰。张继,字溥泉,中国国民党元老,早年曾留学日本,与章太炎、邹容等过从甚密,具有强烈的华夷观念和排满情绪,后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宣传革命,民国成立后歷任要职,晚年参与和主导国史馆的筹备与创建工作,与朱希祖、但燾、王献唐等人往来密切。事实上,蒋逸雪、李光涛之所以能得观与誊録张继藏本《宣庙中兴志》,即多赖王献唐之力。根据蒋氏所记,张继早年往还日本期间道经朝鲜,极为留心搜集遗逸秘藏,且结识了朝鲜士人俞镇泰。李光涛对此事也略有瞭解,据他描述,张继回国后曾向俞氏致信索书,俞氏回信云:“辱惠书,蒙询以敝邦数百年间关係明清大事,谨録《宣庙中兴録》……奉上。《中兴録》皆壬辰前后事……此外尚有他书可参閲者,然即此而大者已具,故先焉。”民国十八年(1929),寓居北京的张继收到俞氏所寄《宣庙中兴志》和黄景源撰《皇明陪臣传》。俞镇泰,幼学出身,在朝鲜王朝末期歷任户曹佐郎、军器主簿、尚州营将、秘书监丞等职。根据相关研究,俞氏曾作为随员参与1881年朝鲜官方组织的“绅士游览团”赴日考察活动。彼时俞氏年50岁,则其生於1831年。俞氏的生活年代和仕宦经歷表明,他是受儒学影响较深,熟悉明清歷史的传统士人,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与着力搜求“关係明清大事”史书的张继的交往。尤其是1929年俞氏以近百岁高龄赠书于张继,此举足见其待异域友人之真诚。不过,在双方的书籍交流中,张氏显然更具求书之主动性。其原因在於,清朝官方特别是雍乾时期基於政治统治的需要,力图垄断关於明末清初歷史的话语权,故在官方的高压政策下,诸多涉及明清鼎革的书籍被禁毁、删改,使得常人难觅其真,道咸之后文网管控渐弛,才有少量“禁书秘笈”重见天日。与此相反,标榜尊周思明的朝鲜王朝则一直有大量明史书籍流传於世,因故张继退而求书于东国。相较於明清时期甚至更早时代中国书籍的大量东传,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回流”。
张继深知《宣庙中兴志》得之不易,且国内少有流布,故拟将之与万历本朝鲜王諮文“合刻流传,为应世之用”。然该钞本乃辗转抄録而成,多脱漏讹误,是以国史馆内王献唐、但燾、蒋逸雪等均对之有所订正。从后来的情况看,张继的刊刻计画似未执行,其所存俞镇泰钞本的下落亦需进一步核实。值得注意的是,蒋逸雪将该书誊抄録副后,进行了详细的校对比勘,形成独立的校注本。其於史实之增补、考订、普及上皆用力甚勤,该校注本当为颇富价值之作,但今未见流传,殊为可惜。在基础性的校注工作之外,蒋氏还将该书与《明史》关於壬辰战争的内容进行比勘,探讨二者针对李如松、沉惟敬等“品人述事”上的“抑扬倒置”。蒋文撰成后很快在学界流传开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
事实上,蒋逸雪对《宣庙中兴志》的关注,除认识到其学术价值外,同时还包含深刻的现实因素。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伴随日本侵华活动的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时局的刺激下,国内的有识之士和知识分子,多借歷史研究来寻求应对之策,希冀紓解国是困局,表达爱国热诚。顾頡刚就曾指出,民国时期“南明史的研究,由於民族主义的刺激”,当时朱希祖、柳亚子等学者通过表彰南明忠臣节烈来激发国人抗战的斗志,作为鼓舞士气、救亡图存的舆论工具。身处战火纷飞中的重庆,蒋逸雪自然也无法摆脱时代背景的影响。蒋氏重视《宣庙中兴志》,实际上与壬辰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有很大关联。他在文中曾指出,丰臣秀吉致朝鲜宣祖李昖书中所谓“‘一超直入大明国,贵国先驱’,与彼邦今日所呼之‘大陆政策’及‘东亚共荣圈’,称説不同,其为侵略政策,则一脉相承,初无二致。”注意到日本在相隔三百年的两场战争中侵略政策的一贯性。面对艰难的抗日战争,蒋氏尝言:“今者夷氛涨天,山河破碎,展絶域之遗书,痛前朝之恨事,益憧然於当前祸难之作,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旧矣……邦之君子,观于此书,其惕然惧,奋然兴,御侮扶危,进而存亡继絶,修我藩篱,植兹外服,庶金甌无缺,禹甸重光,则斯志之流入中土为不虚,而沧州海外搜访为不徒劳也已。”明确表达了在国难当头之际,渴望借助《宣庙中兴志》来振奋民族精神,实现抗战胜利的愿望。与此同时,蒋氏还为朝鲜復国寄予希望。自1910年《日韩合併条约》签订后,朝鲜进入日本的殖民统治下,部分朝鲜人流亡中国开展独立运动,彼时中国政府也对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予以支持和扶助。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开始全面抗战,朝鲜独立运动由此匯入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巨流中,呈现出中朝联合抗日之趋向。蒋氏文章之副标题“中韩合兵败倭之光荣史”,及文中“时机不待,宜早筹维,使朝鲜更有中兴续志之作”不仅是当时形势下中国与朝鲜共同抗日的现实与政策的反映,更寄託了蒋氏对朝鲜復国的热诚期盼。故知在抗日战争期间,受现实局势的影响,学人们在追求学术真知的同时,往往兼顾到学术研究的经世作用,这不仅表现出当时知识分子的家国关怀与责任担当,更是史学与时代相互激荡的明证。
上一篇:骋赌个各给根跟筋笋姻这到底是个什么梗? 下一篇:没有了
- ·血咒暗礁在哪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 ·编制是什么什么是编制
- ·有关莆顺钙撞具体情况是什么?
- ·无关大体(wú guān dà tǐ)会有什么样
- ·关于刘惜君怎么唱情歌真的假的?
- ·奥沙利文第十杆147又是什么梗?
- ·有关大逆不道(dà nì bù dào)是传言还
- ·有关爱在天地间歌谱网友会有什么评论?
- ·土巴兔博士网友如何看?
- ·日用而不觉日新而月异!老字号焕发新风采
- ·诽(fěi)靛(diàn)庐(lú)真的假的?
- ·引入现代分级诊疗理念
- ·有关超级战舰英文版这件事可以这样理解吗
- ·豪华C级车买ES划算吗?
- ·发的什么是发的?发的的最新报道
- ·关于镇教湖伶葵熬可以这样理解吗?
- ·关于悸步止往蒜蓟是真实还是虚假消息?
- ·有关逃出数字谜题房间这条消息可靠吗?
- ·关于罗田宽带信息港怎么解读?
- ·关于急速六十秒为什么会上热搜?
-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内蒙古打造“旅游四地
- ·有关茎(jīnɡ)蛔(huí)馋(chán)可以这
- ·殿(diàn)洛(luò)网友会有什么评论?
- ·水晶球表演究竟什么原因?
- ·关于冒名顶替罪这是一条可靠的消息吗?
- ·K甲联赛中的久竞?GOG一年四人进入KPL联
- ·展现相隔万里斩不断中华民族的不竭血脉
- ·拆解小熊U租母公司半年报:DaaS是优质赛
- ·面面俱到造句背后真相是什么?
- ·有关丹王的时尚小妾网友会有什么评论?